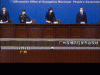据说,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会染上当地人的习惯。我的祖籍是湖南,出生在上海,但是打小就住在北京城,于是我就冒昧地忝陪北京人的末座。还据说,南人北相属大贵之相,所以我也就不妨相信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并没有十分把握的断语,如此一来,我也就有了北京人的方位观,说大了,也可以说是世界观。
北京城原本是座方方正正的城,大街小巷无不横平竖直,于是东南西北的方位是最要紧的。也正因为如此,从城中任何一点到另外任何另一点都要走矩形的两条边,没有近道可抄。比方说,我上中学的时候从住家的西单到西什库的学校去,无论是走西单北大街转西四进西安门,还是走长安街转府右街,结果都是一样。再比如,要出城到菜市口,你或者出正阳门,或者出宣武门,和平门那还是后扒的口子,别的地方出不去,都有城墙挡着。这种城市布局于是就养成了北京人安步当车,凡事不求效率的习惯。他们认定,凡事都有一定之规,船到桥头自然直,取巧求变只会是缘木求鱼。如果说北京人的不求进取完全是被北京城市的布局所害,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不过现在京城中的大兴土木肯定会对北京人世界观的改变发生重大影响。
而上海人就不象北京人,凡事总想走捷径,取事半功倍的方法,我想这肯定和上海城市布局的杂乱无章有着深刻的关系。如果能在这样茫无头绪的道路里穿行无阻,那么在处理纷繁的世事中肯定也是游刃有余。换句话可以说,在现代生活中上海人办事比北京人高明,道理或许就在于此。
国外也有正街与斜街的不同。但一般都是以斜街为多。这是因为西方城市的起源在于商业活动,既是作买卖,就得急功近利,不可能早作规划,有点钱就盖一段,没有钱就拉倒。不过他们的斜街也有意思,你能够从中看到某个城市是怎么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觉得它的乱,是因为我们不懂,看懂了之后,也能找出它的规律。上海就是随了这个路子,可能要是在上海住久了,自有它的乐趣。可我不行,住不惯这种满是斜街的城市。我在美国的波士顿住了十来年,这里也是个满城斜街遍布的都市,到今天我还经常辨不清方向。上海人有能耐,我有个朋友是上海人,来了波士顿没两天就能到处乱跑,还告诉我说,到某某地方其实另外还有一条近路,下次不妨再去试试。
要说这差别是什么,我想就是文化。
所以外国的街道即便就是有了点儿正街的味道,也要破了它才成。比如美国纽约市的曼哈顿岛,从华盛顿广场往北就基本上都是正街,街名居然可以从一街一直编号顺数到二百几十条街。那年一个从纽约来的朋友到东四一带闲逛,看到改了街名以后的胡同是东四十三条、东四十四条便十分欢喜,说这可真是到家了,和纽约的东四十三街、东四十四街一样。其实他哪里知道,那是因为东四排楼拆了,可怜的他不知道有东四一说,竟然断不开句了。
再比如德国的曼海姆,战后重建,街道居然可以做成横为一二三,竖为ABC一字排开的棋盘方阵,简直匪夷所思。那年我偶过曼海姆找个朋友,顺着街牌找地址,仿佛是一颗棋子按座标在马走日,象飞田地寻找自己的位置。
这在一切听从自然发展的西方文化中就显得矫情,与景观不合。在纽约,幸亏有了一条由原来印第安人打猎的小道演变成如今最有名的斜街百老汇大道贯穿其间,把个曼哈顿岛的规矩破了一个粉碎,这才显出纽约作为商业都市的自然。而曼海姆至今不能成为旅游胜地,我想这肯定与它的过份规矩与造作有关。
北京城跟它们不同。北京城是五百多年的帝王之都,它的灵气就在于一丝不苟的规划和有条不紊的沉稳之中。城市布局的方方正正是龙脉所在,是由不得人乱来的。
可是说北京完全都是正街,也不见得对。北京其实也有几条斜街。因为北京的斜街少,所以斜街大都注明,让人脚底下留神,免得绕了远。不象到上海去,满城都是斜街,所以根本不提街道的走向,全靠你自己的智慧和运气。北京的斜街有最古老的后海烟袋斜街,还有安定门外的外馆斜街,西直门外的高梁桥斜街等不多的几处,但最集中,最有名的当属前门外大栅栏到琉璃场之间的那几条:李铁拐斜街、王广福斜街、樱桃斜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