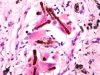与规培生强烈的不满情绪、社会对规培制度的反省相对应的,是官方仍努力正当化规培制度的“剥削性”。2024年8月19日医师节,规培制度发起者之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学科主任刘进回答央视时表示:“适当疲劳状态下还能基本正常工作的能力必须要有,否则你就当不好、当不了这个医生。”这一言论迅速引起了广泛争议。不少规培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所谓的“适当疲劳”只是对规培制度压榨的合理化,忽视了规培生长期面临的过度加班、高强度工作的处境。尽管刘进在讲话中补充道:“过度疲劳、无休止地加班,这些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对于规培生而言,ta们往往已经习惯于加班成为常态、疲劳工作被视为职业必修课的现实,因此这样的补充反而被认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许多规培生反驳道,与其强调“适当疲劳”,不如从制度上保障合理的工作时间与休息权。

规培生的工资保障亦是一个顽疾。由于规培期间的学生身份,规培生没有劳动合同,仅靠每月几百至一千多元的补助度日。据统计,69%的规培生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仅14.5%的收入超过5000元。微薄的收入与其付出的劳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早在2022年,“清零”政策放开后,疫情在短时间迅速蔓延,医院要求研究生和规培生必须留院支援但却未能提供充分的医疗保障和劳动待遇,当时全国超过10所医学院校学生喊出了“同工同酬”等口号(工劳往期梳理)。时隔3年,在各地公立医院频繁传出降薪欠薪消息的今天,合理报酬诉求的实现显得愈发困难。
工劳评论
规培生自杀事件揭示了规培制度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群体长期被剥夺休息权、劳动保障与基本尊严。ta们在高强度工作的压迫下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却因学生身份和微薄收入处于弱势地位,无法通过劳动合同维护自身权益。在主流舆论对疲劳文化近乎默许的氛围中,制度性的劳动剥削愈发显而易见。
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学生群体频繁沦为廉价劳动力?“降本增效”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市场的核心逻辑,而廉价的学生劳动力正是市场化改革下医院自负盈亏的重要手段。对医院而言,规培生是成本最低的“人力资源”,承担着一线医生的劳动强度,却仅需象征性的补助。
而另一边,被输送到工厂的职校生,境遇则更加严峻。职校学生面临学校、劳务中介、工厂多方势力的压迫,各方相互庇护、谋利。职校学生被迫以“实习”名义,低薪从事与专业无关的流水线工作,有时还会因此造成身体和心理创伤。当ta们最终离开学校拿到毕业证书时,却发现自己既缺乏实际技能,也无法摆脱社会的偏见与学历歧视。
规培生与职校生虽在教育系统的序列中存在差异,却共同面临着低成本人力替代品的处境。当我们讨论某一群体的境遇时,更应看到将劳动者利益置于底端、将成本压力不断转嫁给更弱势群体的系统性链条。如何促成不同背景学生群体的联合,推动各自处境的改善,或许是未来值得思考的方向。
相关事件
2024年4月,呼和浩特市公立医院无故辞退40余名劳务派遣护士
2024年10月,欠薪10个月后,公立医院梅州市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倒闭
2024年8月,河南清丰第一医院拖欠工资,医护集体讨薪
搬厂维权
事件回顾与梳理
疫情后,工人集体维权事件频发。据中国劳工通讯罢工地图的有限统计,2024年至少发生了1508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其中搬厂维权事件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尤为频发。。2024年1月10日至14日,上海松江东洋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工人集体罢工,抗议公司不合理的搬迁赔偿标准;3月16日,湖北阳新电子厂一夜搬空,工人不仅没有得到补偿甚至工资也没有结清,遂进行集体维权;4月10日,因烟台凯实工业有限公司搬厂补贴不到位、政策不合理,工人维权两月无果,遂开始在互联网上寻求关注和帮助;7月29日,珠海宝力模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决定搬厂,但拒绝对员工做出任何赔偿,部分工人发起集体维权,要求公司对ta们做出合理赔偿。

工厂搬迁给工人带来的影响有很多,譬如工作场所迁移带来的生活圈移动、通勤时间的变化等。但更为严重的是,工作环境或工作强度等的剧烈变动可能导致工人难以适应,如果工人主动辞职,不仅得不到任何补偿,而且还会失去工作。
在搬厂维权中,一些工人聚焦于争取应得的补偿与合理的安置,另一些则直接抗议、阻挠搬厂行为本身。例如,3月17日,深圳乔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爆发了罢工,要求公司依法支付搬迁补偿金、并补缴社保。该罢工持续了一天,后因政府调停。3月18日有工人发抖音表示,厂方暂停搬厂,工人复工。在维权过程中,厂方试图让工人相信“这不是搬厂”,坚称搬厂一事纯系两位带头工人造谣,但是其自身近期以来的产业部署已然让工人们注意到生产中心的转移,纷纷忧心于个人前景。除此以外,工人们在抗议中同时表达了对公司欠缴社保的强烈不满,超过120名工人联名要求公司不仅承认搬厂的事实,且补缴拖欠的五险一金。

从大多数搬厂维权案例来看,工人很难在搬厂成为既定事实后应对资方的搬迁,不仅难以要求搬迁后的厂方支付经济赔偿,甚至连原本应得的工资也无法确保结清。因此,对于工人来说,在搬厂成为定局之前进行维权,才能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为此,可以将阻挠搬厂的抗议行为,如乔丰科技的工人维权,看作是一种“以生产资料为人质”的维权博弈。
工劳评论
从企业的角度看,搬厂往往是资本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搬厂亦成为企业规避赔偿责任的常见手段。不少工厂“一夜搬空”,企业不仅欠薪跑路,还以迅速撤离的方式规避赔偿,使工人维权难上加难。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操作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制度的“纵容”,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增长目标的驱动下,倾向于优先维护企业的利益,而选择性忽视劳动者权益。
而工人的维权策略也逐渐发生变化,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抗争,甚至在搬厂成为既成事实前进行阻挠。这种“以生产资料为人质”的维权方式,成为工人在资本强势面前的一种博弈策略。工人通过集体停工阻止厂方搬迁,将谈判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而这种策略的前提,正是工人对生产活动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然而,这种博弈策略也存在局限性。即便维权行动取得阶段性胜利,企业也可能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削减劳动成本,例如裁员、调岗或变相降薪。搬厂维权或许难以完全阻止关厂搬迁,但工人的抗争仍会给资方以震慑,而在过程中积累的抗争经验,也将激励相同处境的其它工人。
相关事件
2024年5月,吉林威卡威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人罢工,抗议公司搬迁厂区不赔偿
2024年6月,珠海德资家具厂搬迁不赔偿,工人多日罢工维权
2024年11月,数百工人罢工抵制富士康搬迁厂区无赔偿
此篇年度回顾的完成实属不易。工劳编辑组在讨论追踪后续报道的设想时,便已预料到这种尝试的艰难——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关于工人权益的新闻能够被报道已属不易,想要深入追踪后续更是近乎奢望。而事实也验证了我们的担忧:绝大部分事件,要么已被删帖湮灭,要么早被遗忘尘封。即便如此,我们试图尽可能呈现这些行动和苦难。这是劳动者抵抗的回响,也是对未竟之事的执着守望。新的一年,愿你我继续,共同关注劳动者不该被遗忘的苦难与抗争。倘若可以,尝试迈出行动的步伐,即便只是一小步。
本期撰稿:马乙己、伊甸、蓝水、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