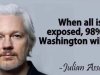哈维尔有时候会亲自在法庭上答辩,特别是如果法官们的正反意见不相上下时。这种情况,想当然会被视为是哈维尔运用个人的权威,来左右法院的意见,以达其目的,但其中有一位法官弗拉迪米尔‧克罗克次卡(Vladimir Klokočka)否认了此种说法。他在Lidové noviny日报发表文章提到:“宪法法院从来不会为了取悦哈维尔,而做出违宪决定,宪法法院的决定都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宪法法院无庸置疑地强化了总统的权威,但也保持了法院本身的自尊与权威。”
那是一幕感人、却多少有些凄凉的退场。哈维尔这位早年的批判性剧作家,在他66岁,十三年总统生涯结束的那一天,2003年2月初的那个下午,在漫天飘舞的大雪中,他在几百位市民和友人的注视下,最后一次检阅总统府外—–布拉格城堡广场上的卫兵交接典礼。保罗.威尔逊感慨著:“他在任的最后一个下午,我观察到,一个渺小而近乎寂寞的身影,身着深蓝色外套,最后一次检阅古堡的卫兵交接典礼,卫兵们身穿宝蓝制服,军乐队把总统乐曲吹奏得漫天响亮,数百人伫立在St. Vitus那既古老又现代的教堂底下──哈维尔对那数百万不在场者所具有的意义,这数百名在场者明白并了然于胸。雪花大片大片飘落,停顿在鹅卵石路上。我心想:不论他有多少缺失,这样的人生不是非常奇妙吗?”
令我难以想像的是,那几百人是十三年前,(1989年11月17日到12月30日)和平革命期间那几十万捷克人民的化身吗?抑或,他们可否代表十三年前的他们。那时,数十万捷克人民聚集在布拉格的温斯莱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他们面对成千上万的镇暴警察高呼:“还给我们吧!政府。”“共产党,下台!”也是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当共产党政府宣称他们代表人民,并恐吓广场上的群众不要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时,广场上聚集的几十万群众高呼:“我们才是人民。”那时,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异议份子领袖,哈维尔日夜置身于人民之中,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之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er Dubcek)及反对运动团体“公民论坛”(Civic Fourum)的成员们一起,站在可以俯瞰广场的前麦兰垂克出版社(Melantrich)阳台上,用扩音器不断地向人民发表演说,用和平、坚定、不容质疑的声音要求共产党移交权力。接着,在政府大厦的共和国宫中,哈维尔作为一位突然出现在共产党政府总理和部长们面前的“公民论坛”灵魂人物,代表着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从容,用冷静、沈稳但是不容置疑的分析劝说共产党交出政权,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下台。经过冗长的谈判,最后,共产党终于在人民的力量和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会再动用苏联军队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下,被迫接受下台的请求,交出政权。随后,1989年12月28日深夜,哈维尔和他的同志们缓步走到俯瞰广场的前麦兰垂克出版社阳台上,在无数摄影镜头下,向深夜守候在广场上的几十万人民宣读“公民论坛”和捷克共产党政府代表谈判结果的公告。接着,是人民那撼动天地的欢呼和叫喊,人民们高呼:“哈维尔,哈维尔”、“哈维尔,当选”、“哈维尔,总统”,并将这声音传递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十三年之后,人民的激情早已冷却,他们对哈维尔怀着敬意(而不是激情)以及日渐增多的抱怨,此时的哈维尔,再也不能像1990年代初那样,随便一个老熟人或朋友都可以敲门走进总统府找他喝上一杯了。“人民”们说,我们也不可能在布拉格街上碰到哈维尔或在街头某个转角的咖啡馆和哈维尔聊上一会儿了。批评者说,他已远离了普通捷克人的生活,说他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和投入超过了对捷克民间疾苦的了解,甚至说他更像是一个住在捷克的外国人。
无疑,哈维尔结怨甚多。首先,哈维尔不属于任何政党,故,他从来不去取悦选民。他和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糟,或者说,议会中的共产党议员处处和他作对。他坚持,只要共产党没有为过去所犯下的罪过诚心认错,他就永远不会原谅这个政党。同时,由于他的再婚,或者说由于妻子是位在共产党时代就走红的电视明星,由此招致了不少的攻击。有时,媒体或他的敌人将他形容为是一个精力耗竭,并被野心勃勃的美艳妻子所奴役的病人,是一个身居王位却又处处对人对事持着异议的孤家寡人,认为他对于议会民主完全外行,说他已经过气却还恋恋不舍地握著权力不放。据说,他和伊万(Ivan Havel)———那位曾在他早年的牢狱生涯中给予他巨大的思想和感情支持的亲弟弟,由于家庭财产分配上的分歧,关系也出现了问题。
然而,即便如此,哈维尔离任时,在捷克人民中仍享有55%的支持率(虽然他就任总统时的最高支持率曾达87%),这是任何国家的总统或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比率。
担任总统时的哈维尔每个月月薪约合二十一万台币,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周,捷克议会曾就共和国首任总统退休后,是否应按照民主社会的惯例支付每月约七万元台币的退休金,无偿提供办公室、专用轿车、安全警卫及终生的全职司机这一法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现任总统克劳斯的政党民主社会党和捷克共产党的坚决反对下,这一提案被拒绝了。也就是说,哈维尔作为捷克历史上第一位体面退休的总统,没有民主制度下前总统应有的待遇。然而,作为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品牌”(捷克总统克劳斯带着嘲讽的无奈之言),哈维尔全然不必担心可否维生,因为哈维尔有着永远也应付不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邀约,假如身体状况允可,他完全可以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那样,以在世界各地演讲谋取厚酬(我估计,他的一场演讲酬劳至少应有两万美元)。
然而,他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1999年,我的友人,也是哈维尔最信任的中捷文翻译、捷克查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然(Olga Lomava)教授就告诉我一个在捷克流传的说法,说哈维尔除了脑子之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修补过的。他的肺和肠均因癌症切除大半。年,也就是他的元配妻子奥尔嘉过世那一年,他曾七次被送进医院抢救和施行手术。那一年,哈维尔面对着生命中最大的挑战,他的妻子奥尔嘉(Olga)在一月去世、十二月他也因肺癌而濒临死亡边缘,当时他高烧不退,双目几乎失明,医生开始时只是诊断为一般性肺炎,后来才确定是癌症,并立即切掉了他右边的半个肺。在上手术台前,哈维尔还在抽烟。据说,当时住在加护病房的哈维尔,有一天突然呼吸困难,护士竟不在旁边,正巧达格玛去探望他,达格玛吓坏了,拼命呼救,并及时招来医生,紧急抢救,使哈维尔活过来了。1997年1月,哈维尔和达格玛‧维什诺娃(Dagmar Veškrnová)结婚,达格玛是捷克最著名的电视剧演员,在捷克民众中家喻户晓,她是哈维尔的情人,并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他的生命。
然而,由于那位和他厮守一生,共过无数患难的妻子奥尔嘉的形象深入人心,捷克老百姓难以谅解哈维尔这么快就再婚的举动。一九九九年夏天,我曾专程去布拉格公墓瞻仰卡夫卡和奥尔嘉的墓地。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午后,奥尔嘉已过世三年多了,可她的墓前仍摆满了鲜花,前来瞻仰和送花的人络绎不绝,可见人民是多么地怀念她。
为此,哈维尔不得不通过电视演说向全国解释道:“在奥尔嘉去世前,她说过我可以再婚。”哈维尔说:“那时,我根本没有这个念头,我已决心独自走完自己的人生。但她坚决认定我不可能一个人生活,也不应该这样。她是对的,而且生活也证实了这一点,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达格玛。”
为了疗养他那由于几十年的吸烟习惯和牢狱生涯伤害了的肺部,他在葡萄牙空气清新的Olhos d’‘Agu海边买了一栋别墅,他会不时地在那里住上一段时日,休养,也是为了躲避他称之为永远也做不完的“一千零一件事”所形成的工作压力。不久前,他接受捷克报社的采访中抱怨说,他的秘书和助理,从当总统时的近百人变成只有三个人。
而他现在的机要秘书,也就是我近来唯一打过交道的一位,显然是个冷面、一板一眼、专门替老哈挡掉杂务的家伙,他的英语有时写得和我一样烂,始终也拼不对Taiwan(台湾)的六个英文字母,而且他答应替哈维尔寄我的照片电子档也永远寄不出来。然而,有一点他却是绝不会写错的,在e-mail中,他对老板哈维尔的称呼总是毕恭毕敬,均尊称哈维尔为总统,而不是哈维尔“前”总统。
哈维尔的早期总统生涯中充满了自由甚至畅所欲言的平等气氛,我惊奇地发现,在他1990年代的总统府内,没有太多的官僚气息和体制化的死板仪式。1991年,在他和他的老友、波兰著名异议知识分子领袖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进行的一场内容广泛、思考深刻的重要访谈中,陪同他的助理(从国际事务发言人到新闻秘书)均可以随意插话,甚至抢话头、打断哈维尔的言谈,以对他的想法表示异议。他和米奇尼克对话的方式尖锐、风趣、直言不讳,是我读过的所有哈维尔访谈中最精彩的。请看他们一开始是怎样进入对话的:
哈维尔:“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
米奇尼克:“对了。”
哈维尔:“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
米奇尼克:“你很有经验,因为你曾经多次接受长时间的审讯。三个小时对你这样的一个老重罪犯来说,不算什么。”
哈维尔在国际事务中所做的一件最有争议性的事,就是从2001年以来,多次表示支持美国布希政府对伊拉克的武力政策。在2003年2月他离任前,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报纸《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出现了一封由哈维尔及其他七位欧洲的领导人联合签名的信,内容是完全支持布希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行为。为此,他受到了早年许多支持并声援过他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谴责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