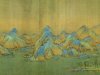当时,宋朝主动关闭了边境榷场,并停止了对西夏的大宗“岁赐”,就连西夏一向赖以出口赚外汇的“青白盐”也被宋朝禁止入口。为此,李元昊即便赢了战争,也不得不向宋朝低头。于是,李元昊仿照先父当年进献500匹骏马帮宋朝修陵之例,向宋朝敬献良马50匹,求宋朝赐佛经一藏,以此来试探求和的可能性。
没想到,宋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请求。之后,李元昊又组织僧人翻译西夏文《大藏经》,并让译经经验丰富的回鹘僧人白法信和白智光等高僧组建研究团队。从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到民安元年(1090),该团队利用53年时间完成了3579卷西夏文佛经的翻译。
由于西夏控制了丝绸之路,天竺的僧人进入东土传法,必须经过西夏地界。李元昊为了留住这些僧人,提前派人守住交通要道,待他们前来,极力截留。如遇僧人反抗,西夏士兵则就地将其羁押,好吃好喝供着。
李元昊的崇佛之念由此可见一斑,但西夏人野蛮的行为还是给过路僧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们口耳相传,很快,丝绸之路在失去东、西方贸易的同时,彻底失去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
而李元昊强势霸占僧人的背后,是佛教成为西夏全民的普遍信仰。西夏境内的瓜、沙、甘、凉及兴庆府等重要城市,护国寺、感通塔、崇圣寺、卧佛寺、大觉圆寂寺等大型佛教建筑拔地而起。

▲始建于西夏的张掖大佛寺卧佛。图源:摄图网
佛教的介入,也让西夏的帝王们普遍相信,自己与佛的感应是无时不在的。所以,在修建帝王陵园时,西夏的帝王总会给佛祖让出子午线上的位置,在其右后方为自己建造陵塔,同时于墓室内大量绘制佛教壁画,以达到“事死如事生”的目的。
然而,佛教的兴盛对李元昊而言,却是要命的。
他生性暴虐好色,多猜疑,犹喜强夺他人之妻。当时,他中了宋朝大将种世衡的离间计,杀了西夏“台柱”大将野利遇乞,并将他的妻子没藏氏发配到兴庆府的戒坛寺出家。没藏氏婀娜多姿,李元昊管不住下半身,遂常常到寺中与她幽会。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二月,李元昊的幼子李谅祚出生。
为了让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将来能继承西夏皇位,没藏氏与兄弟没藏讹庞合谋,设计让李元昊霸占了太子妃。太子李宁令哥怒不敢言,后在党项权贵的怂恿下,才于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的元宵夜趁着李元昊酒醉之际,闯宫削掉其酒糟鼻,使西夏一代开国之君在惊吓中一命呜呼,享年46岁。
官方记载,李元昊驾崩两个月后,被群臣葬于泰陵。但,考虑到西夏王陵的形制与宋陵类似,这则史料的准确性至今仍被不少学者质疑。

自李元昊之下,西夏诸帝始终遵循汉人的规矩建陵,并形成独有的陵园形制,但历经数百年的风沙,待大明庆王朱栴造访时,那里却成了一座座巨型土锥。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在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朱栴在编写《宁夏新志》时也只能采信自己道听途说的内容,而没有继续探查下去。
直到朱栴去世五百多年后,这些巨型土锥的身份才第一次被人们重新定义。
1971年,兰州军区空军某部在宁夏贺兰山下修建军用机场。几个战士在挖掘工程地基时,意外发现了一些刻有不明文字的古代陶制品。鉴于当时黄河流域时常有重大考古发现,部队立即暂停施工,并将此消息层层上报,电请宁夏地质博物馆筹备处介入。
当时,宁夏博物馆原馆长钟侃刚被调入地质博物馆筹备处工作。接到消息后,他第一时间便和同事王菊芳、李俊德、邓乘浩等人赶赴施工现场。
在方圆五十八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钟侃等人看到了许许多多残垣断瓦上刻印着一种形似汉字却又不是汉字的文字。钟侃立即想起数年前在青铜峡108塔考古时,也曾发掘出写有这种文字的佛经。那时,在场的考古专家一致断定此乃失传多年的西夏文字。
所以,眼前出土的断垣残瓦,极有可能就是西夏遗存。
不过,考古学向来讲究证据。钟侃等人回到筹备处抓紧时间翻阅各类古籍,直到在《宁夏新志》中看到朱旃留下的记载,这些巨型土堆的考古方向才最终被确定。
1972年,在贺兰山脚下发现西夏李元昊墓及其他八座王陵的消息轰动全国。随后,在全国各界的共同支持下,考古学家借助电脑动画技术,初步模拟复原出西夏王陵最初的模样。
原来,这些建于黄土高坡上的王陵每座都由月城和陵城相连组成,平面呈“凸”字形状,陵园内单体建筑角台、阙台、碑亭、献殿、陵塔及附属于陵城门的门阙和角阙的平面分布基本与中原王朝相同,形成西夏陵园群体建筑的基本格局。

▲西夏王陵俯瞰。图源:摄图网
可是,当考古人员仔细对地面残存的遗迹进行测绘时,又惊讶地发现这九座高耸的土堆似乎并非简单的昭穆排列。在新测绘的图纸上,人们看到了一个类似北斗七星阵法的排列顺序。除此之外,依附各大王陵的陪葬墓也呈现一种众星拱月的姿态,似乎更证实了当年西夏王陵的设计不仅参照了中原帝陵的规制,更有自己独创的一套陵园制度。只是这一切的秘密,专家们尚未能从残存的土锥上找到确切的答案。
在整个探查过程中,唯一令人感到庆幸的,就是语言学家李范文借助苏联学者聂历山的《西夏语文学》、罗福成的《同音》写本等资料,汇编出了第一版《夏汉字典》。这是一本专门用于翻译西夏文字的工具书,借助相关研究,考古学家们终于在7号墓中找到关键性的记述文字:“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
大白高国是西夏的别称,圣德至懿皇帝即西夏仁宗李仁孝。也就是说,7号墓的主人正是西夏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李仁孝。
由于中国古代普遍采取“五音姓利”的理论埋葬先人,所以,考古学家在确定西夏陵的昭穆排序后,又根据姓氏结合五音、五行的做法,按辈分主观地将1号陵、2号陵陵主认定为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据此类推,3号、4号、5号、6号陵则分别被推测为李元昊的泰陵、李谅祚的安陵、李秉常的献陵以及李乾顺的显陵。
见证了一个王朝近两百年风云的九座王陵,只发掘出这么一点有用的信息,显然无法满足世人的求知欲。于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又被提了出来:究竟是谁破坏了这些王陵?又是什么原因把它毁坏得如此彻底?
不少学者将矛头指向了成吉思汗。因为,最终导致西夏国灭亡的,就是这个像大海一般的可汗以及他手底下打遍亚欧大陆无敌手的蒙古铁骑。
从1205年到1227年的22年间,因西夏挡住了蒙古铁骑西进的步伐,在成吉思汗的命令下,蒙古人与党项人之间爆发了六次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结局两败俱伤,成吉思汗在出征途中命殒大西北,而西夏军队在蒙古铁骑的压制下,战至最后一人。胜利者终归有对失败者的最终处置权,成吉思汗临终前,密令手下屠尽党项人——这一条“罪证”也成了专家们认定蒙古大军破坏西夏王陵的最佳佐证。
然而,目前并未发现成吉思汗下令拆毁西夏王陵的直接记载,一些学者认为,在成吉思汗驾崩及西夏故地初平之际,大规模盗发毁坏西夏王陵的行为并不能消灭残存党项人的斗志。反之,因为陵墓的特殊性,蒙古军队做法还易引起被征服者的仇视。所以,蒙古军队破坏西夏王陵的可能性不大。
一种可能性的推论是,西夏王陵乃明朝军队破坏的。
根据史料记载,明代初期,驻守在宁夏的蒙古军队撤退到贺兰山以西一带后,王陵附近就成了明朝边防的第一线。那时,明代经济疲软,要想快速建成一系列攻守兼备的军事要塞,只能就地取材。如此,在贺兰山东麓沉睡了三百余年的西夏王陵就成了绝佳的建筑取材场所。
朱栴之子、安塞王朱秩炅的《古冢谣》写道:
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
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在朱秩炅眼中,这些古老稀疏的巨坟高低错落有致,依稀还能从形制中看出这是昔日王侯百年安居之所。如果这些王陵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被毁坏,这位王爷又怎能看出其中的门道呢?
西夏王陵被谁所毁的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但,西夏王陵留存的遗迹却未被遗忘。今天,进入西夏王陵博物馆前,游客们总要对着门前雕刻的四个西夏文字“大白高国”进行一番点评。谁又想到,曾几何时,那也是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对西夏文字传播天下的一种憧憬呢?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97
钟侃等:《西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79
唐荣尧:《神秘的西夏》,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崔红芬:《西夏时期的河西佛教》,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刘临安、潘静:《西夏王陵与北宋皇陵空间结构的比较》,《文博》,2006年第1期
单爱美:《唐与北宋帝陵比较研究》,《丝绸之路》,2015年第20期
贾寅超:《揭秘西夏陵》,纪录片,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