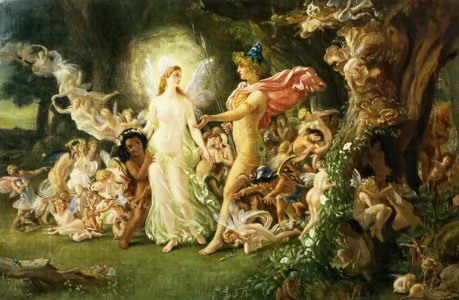第二层,就是在哈姆雷特这位王子身上有着前述的几部历史剧君主人物所没有穷尽或没有深入挖掘的东西,为此莎士比亚不惜新创一部戏剧尤其是悲剧予以展示。也就是说,哈姆雷特与哈尔王子、理查二世、亨利六世等君主有很多相似的方面,但更有迥异之处——在哈姆雷特身上体现着更为浓烈的时代特征。上述几位人物局限于各自生活的时代,例如,理查二世生活于14世纪,哈尔王子、亨利六世则生活于14、15世纪,此时的英格兰虽然开始步入早期现代的潮流,但相比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乃至意大利周边直到北海周边的西南和西北欧来说,早期现代的时代风潮,人文主义、市民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复兴诉求,甚至对于罗马教会的人文主义批判,凝聚民族国家的某种殷切期望,等等,这些发端于地中海沿岸意大利诸邦国的新潮流,在红白玫瑰战争时期的英格兰王国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成长,只是呈现出些许的端倪,莎士比亚似乎也很难进一步发挥,这致使他的四联剧笼罩在传统的都铎王朝历史叙事的神话解释之中。显然,莎士比亚不甘受制于都铎史观的约束,他要展示其独特的英国历史观,尤其是要深入展示那些决定英格兰王国特性且深受早期人文主义浸润的王国君主的生命内蕴和精神实质以及悲剧性命运,因此他选择了一些隐喻,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以及王子复仇的故事就成为他的载体,莎士比亚试图把在两个四联剧中意犹未尽的东西淋漓尽致地表述出来。
一般的文艺批评家把《哈姆雷特》视为一种新的悲剧形式,有别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他们认为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创造出一种新的戏剧类型,即性格悲剧,并从文艺学的历史流变中将莎士比亚视为一代宗师,由此开启了现代浪漫主义。从人物性格方面解读哈姆雷特以及莎士比亚的王朝历史剧,当然有一定的意义,也符合某种真实的情况,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确实展示了人物的生命本质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死抉择的灵魂拷问,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觉醒的意义。对此,19世纪以降的一系列浪漫主义大诗人,诸如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法国文豪雨果、德国浪漫派诗人施勒格尔兄弟等,都对莎士比亚的戏剧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莎翁悲剧突破了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之藩篱,展现了人性的内在本质力量及鲜活的生命力,从而把莎士比亚的戏剧提升到一种浪漫主义的典范地位。相比之下,对于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的分析,还是德国思想家黑格尔论述得最为精深,他在《美学》中对莎士比亚以及莎剧人物哈姆雷特、麦克白、奥赛罗、理查三世,等等,都是从浪漫主义的视角予以分析的,认为他们展现了精神的深厚本质。当然,黑格尔对于"浪漫剧"的理解具有其精神哲学的独特含义,但无论怎么说,莎士比亚戏剧开辟了一种新的戏剧范式,对近代市民主义文化艺术之兴起,无疑具有指导性意义。
通观莎士比亚三十多部戏剧,应该指出,他确实深受近代人文主义的影响,创造的诸多人物,包括君主人物,都超越了各自的身份和地位之束缚,具有人本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思想内蕴,体现着某种人的觉醒,即从封建王权和基督教神权统辖之下挣脱出来的人的觉醒。由此观之,哈姆雷特复仇之际的某种犹豫、迟疑乃至忧郁、迷惑和痛苦,并非仅仅作为王子的心灵挣扎和人生拷问,还超越了这种封建身份上升到一般人的角度,对生与死及生命价值和意义做出生存论式的追问,著名的哈姆雷特自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个人生抉择就不再是仅仅属于王子的,而是属于任何人的,每个人处在一些人生关口,都会油然产生这样的生死之问。这样的哈姆雷特问题,显然是要经历一番人文主义的洗礼,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影响之后,才能产生出来,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不可能激发哈姆雷特生发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