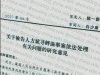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法委透露,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将进行修改完善,并已启动法律修改调研,有望在法律上排除靠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分析人士认为,制止刑讯逼供最有效的方法是将“被告人口供”排除在证据之外。
北京《新京报》报道,《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三部诉讼法,已经连续两次进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刑事诉讼法》1996年进行了首次大的修订,明确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写进法律。但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赵作海等错判杀人、以及拘留所发生的躲猫猫死、喝水死案等反映出的警方和检方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司法监管漏洞,暴露出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急需完善。
报道称,对于公众最为关注的刑讯逼供问题,有学者开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为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中策为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下策为废除现行法中的“如实供述”。
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原就此表示,中国专家提出的上策、以“沉默权”为核心的“米兰达警告”是美国刑事诉讼的规则,但在中国并不适用,因为中国很多案件的审讯过程不透明,即使被告方受到刑讯逼供也没有第三方监督,更不要说被告行使沉默权了。刘律师认为,制止刑讯逼供最有效的方法是将“被告人口供”排除在证据之外。
“证明人,被害人的陈诉、被告人的供诉等等有七、八种,如果去掉被告人的口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管你是允许供诉还是不允许供诉,口供不能作为证据,这样他就没必要刑讯逼供了。”
刘律师说,除了将“被告人口供”排除在证据之外,中国刑法中有关“监视居住” 强制措施等也应该去除。
“目前从监视居住来看,更多的成了变相的羁押,只是不把你关在看守所,而在外面的宾馆,某一个地点,看守所你还有放风的时间,可以定时会见。那监视居住在实践中实际上限制得很严的。还有一个保护家属会见权的问题。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会见家属的权利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规定公诉机关的指控法院没有权力更改。这必须要有民事诉讼法来加以明确。”
据报道,中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1991年由中国全国人大制定,2007年曾做过修订。北京维权律师李静林认为,要修订现行的《民事诉讼法》,首先应该废除“专门立案审查程序”。李律师说,正是因为这一程序,让法院有理由对诸如“三鹿毒奶粉受害人赔偿案”等法院认为棘手的案件不予受理。
“我以为这是完全用不着的。因为他的立案审查,它真正的案件其一该它法院受理的它受理;其二,不该它受理的它照常去其他部门去找。这问题其实很简单,你既然要告之,那就直接告之就行了。那就是告状的人败诉,为什么不做?就是为了他们能少管些事就少管些事。”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1989年通过,已经实施21年。报道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人士表示,已着手开始《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工作。《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由于案件受理范围规定为具体的行政行为,不包括行政部门的各类规范性文件:通知、意见、红头文件、会议纪要等,因此这些文件的出台缺乏必要的监督,导致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李律师说,现在有专家建议,修订后的中国《行政诉讼法》应该对“红头文件”进行监督,但在他看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非常难。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党委决定交政府执行。法院只是起保证作用。法院的院长在共产党里是进不了常委的。而政府的高官他就是常委。党委的决定交政府来执行的事务,它才会有那么一些红头文件来保障政府的执行力。而法院要去把它搞定了,那是不是在和党委过不去?”
李律师认为,中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博弈主要应在政府的公权力与公民个人或团体的私权利之间展开。但是就目前中国的大环境来看,法律无论如何修改,恐怕还是会赋予政府公权力以充分的自由,而忽视对公民个人或团体的私权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