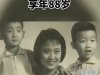知名教育学者、历史学者、作家傅国涌先生,于2025年7月7日凌晨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59岁。
热搜榜自然是没有的。消息还是昨晚一个江苏的朋友传给我的,惭愧。
彼时的国内,水深,火热,丽江也正逢雨季。他的猝然离世,犹如眼前又一盏灯熄灭了。
真是哀伤的一天!
我与他素未谋面,人生亦无交集,但在领域、主张和实践上多有契合之处。
自幼嗜书,考入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师,20世纪末踏上写作之路,二十余载笔耕不辍……
历史学者的他
傅国涌作为独立学者,无博士学位与高级职称,却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独具特色。
其《金庸传》以平视、客观视角刻画金庸,不阿谀、不隐恶,虽让传主"不高兴",却被专家誉为"历来质量最高且最有影响的金庸传记作品"。
他的研究聚焦近现代社会转型,尤其关注百年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及近代企业家本土传统,摒弃宏大叙事,善于从私人记录中发掘历史真相。
如《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通过梁漱溟、胡适、竺可桢、沈从文等人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以个体生命体验折射大历史。
他秉持"用资料说话",《追寻失去的传统》等著作追溯言论自由与公共空间兴衰,为当代提供镜鉴。
受信仰与启蒙思想影响,其作品动人之处在于兼具"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公共写作的他
傅国涌更是积极介入社会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
2000年代媒体相对开放时,他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对重大是非问题能及时回应。
凭自身正气、热情与才华,鲜明表达立场,从言论史研究者转变为"以言报国"的实践者。
其公共写作涵盖教育、社会公正、历史反思、现实批判等广泛领域,观察敏锐,见解独到,兼具学者严谨与公共写作锐度。
他的时评以史为鉴,文风朴实,无学术腔与八股调,立场坚定,言辞锐利。
如此表达需要勇气,而他从不畏惧,"有意见从来不含糊,总是直率地表达"。
直到生命最后一天,他仍在关注社会热点,仍在为公平正义鼓与呼。
教育实践的他
当言论空间受限,傅国涌选择转向教育领域,2017年放弃史学研究,创办"国语书塾"。
当整个教育系统陷入"分数至上"的癫狂时,这个位于杭州老巷深处的小小书塾,成了功利教育汪洋中的诺亚方舟。

他开设"国语书塾",就是与童子一起读书。读书分在家读和走出去读,也就是"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相结合。
在他看来,教育应立足广阔天地、直面伟大文化遗产。他采用"开门办学"模式,践行"行走的课堂"。

雪中吟诵《湖心亭看雪》
他带着孩子们在西湖边朗诵《诗经》,到富春江与严子陵、郁达夫对话,到兰亭与王羲之对话,到绍兴与鲁迅对话,到清华与陈寅恪对话。
在雅典卫城演绎莎翁戏剧,在比萨斜塔下探讨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在但丁的家门口诵读《神曲》。

他还开戏剧教育课和演讲与辩论课,尤其重视儿童作文。在他看来"作文是生命的流露,是思想的体操"。
他认为写作不仅是语言表达,更是思维训练与人格养成,反对应试作文的套路化与虚假性,鼓励孩子观察生活、真诚表达。
带学生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他不要求写观后感,只让孩子们给78年前的遇难者写一封短信。
"我不是给你一滴水,也不给你一杯水,一桶水,而是呈现一幅江河归入大海的画面,看你拿的是什么器皿,打多少水取决于每个孩子自身。"
傅国涌始终谦逊热忱,与孩子平等交流、共同探知,无严苛纪律却富思想吸引力,不灌输标准答案而留足探索空间。
他坚守"育人"而非"育分",虽学生数量有限,但孩子们的表现超乎想象。
11岁的郭馨仪将未名湖的绿比作"司徒雷登的眼睛",13岁的冯彦臻在大明宫遗址前发出"我是一朵历史的云"的喟叹。
12岁的林小棠在日记里写"《诗经》里的蒹葭是未接的视频通话",傅国涌在旁批注"比王国维的'境界说'更懂当代"。
而他的学生付润石在德国游学后,竟写下洋洋四千字《德意志如是说》,那些"文科误国""文科就是坑"论者该"如是说"?
傅国涌带着孩子读书、行走,从不只为纸面知识的获取,而在于一个大写的"人"的展开。
"让他们各自成为席勒的'审美共和国'和雨果的'思想共和国'"
"历史不是为了让人哭,也不是为了让人笑,而是让人明白"
"一个人一旦拥有精神生命就不会死。你们能建立起这样的精神生命吗?如果建立起来了,你们也跟曹雪芹站在一起了"
"教育是不追求成功,只追求成人,是成全你自己"
他胸怀赤子之心,跟着孩子们读了一些原本不会读的书,《苏菲的哲学课》《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等等。
"五十岁开始带小孩读书,过去五十年仿佛归零,我体会到了与孩子一起成长的生命的大欢喜。"
"三百千万(三年百课千人万里)——与世界对话"课程,活的课堂、真的导师、美的巡礼。

跟孩子们"与枫叶对话"
傅国涌,真性情,真话语,真育人。
当其他学校在培养考试机器时,他在培育会思考的芦苇。
当校长们在培养精英时,他在挽救人。

一个时代的精神遗嘱
斯人已去,留下了太多未竟的事业和未完成的思考,这是最令人痛惜之处。
如果天假其年,他的时评、教育写作、海外教学行程一一实现,会有更多孩子承载着他播下的种子,抽枝散叶。
他的尖锐声音,庶几能唤醒更多人,像那位勇敢砸破车窗的青年,发出几声铁屋中的呐喊。
傅国涌,被命运选中的"破局者"、教育功利化时代的"逆行者"、一个犬儒时代的"精神纵火犯"。
最好的纪念不是眼泪,而是继续追问:我们该如何面对历史,如何书写未来?
傅国涌曾说: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家和教育家。只有这些人在这个民族里还有说话、思考、实践的空间,这个民族才处于正常的状态。"
"知识分子最大的使命,是让社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清醒。"
在悼念金庸的文章中,傅国涌写道:"我们将继续追问、寻找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他依然与我们同在"。
希望他关心的教育问题、历史课题和社会正义,将继续被追问和探索;他的著作和精神,将依然与我们同在。
他常说:"毕生事业是'读书',著书还在其次。"
对我来说,还有一样,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