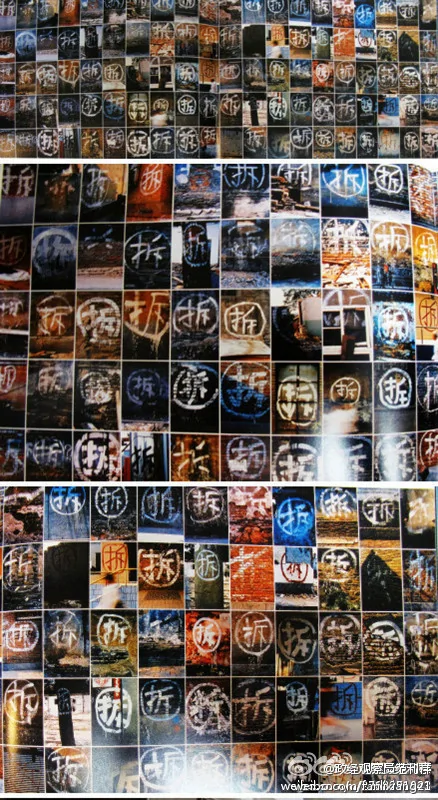论及吃喝,当是国粹,外邦无可出我右者。六大菜系,八大名酒,宫廷筵宴以及那遍及大江南北的各种美食,无不显示我中华饮食文化的灿烂辉煌,源远流长。近年来,中国大陆官场的吃喝之风更是张扬得可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幅吃遍五洲喝遍四海的豪气。
然而,倘若吃喝之时都是只掏自己的腰包,花老婆的银两,本也无可厚非。然而,那吃吃喝喝的开销往往向“老公”身上摊派,都由“老公”兜着。其实,这“老公” 并非那“老公”。这“老公”名义上是“公家”,其实就是咱老百姓,或者换个说法就是纳税人。日前,河南省信阳市的市委书记不是说他们制订了“午饭禁酒令”,半年时间就节约了4300万元的酒钱么。可知他们在禁午饭酒之前每年到底喝去了多少酒钱!公款吃喝的发达弄得上峰几乎每年都要接二连三地下发红头文件,三令五申禁止公款吃喝,但那些“禁令”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国库的银子仍旧不可遏制地哗哗啦啦往外流。于是,中央就规定了“工作餐”不准超过“四菜一汤”。但老百姓看到的是什么呢?那是“四菜一汤,因人配方;四菜一汤,四盆一缸;四菜一汤,糊弄中央。”实际上,即使党中央规定了“一菜一汤”,那地方上照样可以变出各种花样来,国库的银子照样往外流。记得,前些年媒体给出的数据是每年公款吃喝要花掉2000~3000亿元,而最新的数据是2005年已达 6000亿元了。那么,2006年呢?2007年呢?就更是天文数字了。
公款吃喝的发达,伴随着生出许许多多有关吃喝的民谣来。“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不吃是白痴。”看来只有穷吃穷喝才能提高智商了。“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肠子喝坏了胃,喝得单位没经费,喝得老婆分开睡,喝得群众有意见,纷纷告到纪委会。”这民谣说明了群众的情绪,愤愤然也。然而,这首民谣的结尾更有意思:“纪委说,实事求是最重要,能喝不喝也不对。”虽说这民谣把纪委奚落了一通,但实际情况是官场的贪污腐败前腐后继,大案、要案、窝案、串案多如牛毛,纪委哪里会去管什么公款吃喝。纪委不管吃喝,那就由老婆管了,老婆告诉赴宴的老公:“多吃菜,少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其实,今日的官员们,菜没少吃,酒没少喝,但到底是听老婆的话,还是听二奶、小蜜的话,老婆是心知肚明的。至于到底跟谁走,那就要看哪里的钱多了,大款呀,黑帮头子呀,不一而足。
公款吃喝不仅成了极为平常的小事,在一些人的眼中,这吃喝的本事还成了某些“公仆”能力的象征:
能喝四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
能喝五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要提升;
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要调走;
能喝白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
这首民谣的另一版本是:
一口全喝光,这样的干部要到中央;
一口见了底,这样的干部要抓紧提;
一口喝一半,这样的干部要再锻炼;
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党放心;
能喝一斤喝八两,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得调走;
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
当然,这首民谣的调侃意味较浓,但也却有些“公仆”的官位是随着酒量的提升而提升的,是“早上围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而转上去的,尤其是那些高官的“跟屁虫”,即那些善于吹牛拍马的秘书们往往是靠酒量爬上去的。官员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逐渐提升了酒量,也提升了官职。于是,越喝越大胆了,一场豪饮之后,一些“公仆”面红耳赤,另一些“公仆”则是人仰马翻。每逢这种时候早有秘书安排了好戏,也就是小蜜,或曰“攻关小姐”从旁伺候,那些小蜜是何等人物,口中甜言蜜语令官员飘飘欲仙:“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俺给领导来敬酒。您在上,俺在下,您说几下就几下;您在上面好辛苦,俺在下面好舒服。”这是百姓为小蜜设计的民谣,看出小蜜的淫声秽语了。实际的情形可能更真切:“喝百口,喝千口,美女小蜜任你搂;要喝就要喝个醉,醉了二奶陪你睡。” 这就是今日官场的写照。
更有人将老毛的《长征》来了个改头换面,变成了描述官员们吃喝的民谣:“公仆不怕吃喝难,千杯万盏只等闲,生猛海鲜腾细浪,鸳鸯火锅走鱼丸,新式烧烤严冬暖,冰镇啤酒酷暑寒,更喜小姐肤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这可比老毛的诗形象多了。
官场吃喝的档次是随着官阶的不同而大相径庭的:“村级干部吃饱,乡级干部吃好,县级干部吃草,省级干部吃鸟。”其实,吃饱、吃好已经够意思了,媒体不止一次报道有些村里几个干部每年吃掉几十万的公款,那公款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呐。县处级官员当然就要在吃喝中加些“草”了――也就是加些中药的滋补药材之类。而更高级的省部级官员“吃鸟”,此“鸟”并非bird,而是牛鞭、驴鞭之类,这可是胜过重庆市那位宣传部长经常装在文件夹中的美国产壮阳药物“伟哥”的。
关于吃喝的民谣当然不止如上几则。中国的百姓实在是聪慧有加,面对着当今的官场哼出令人捧腹的民谣来,但想想那些下岗工人、贫苦农民的惨状,你还能笑出声来吗?
--------------------------
原载《议报》